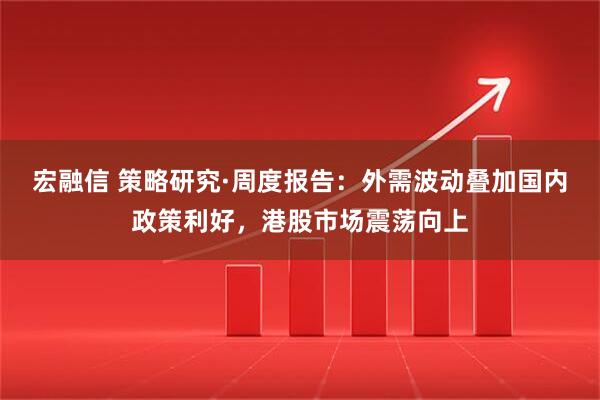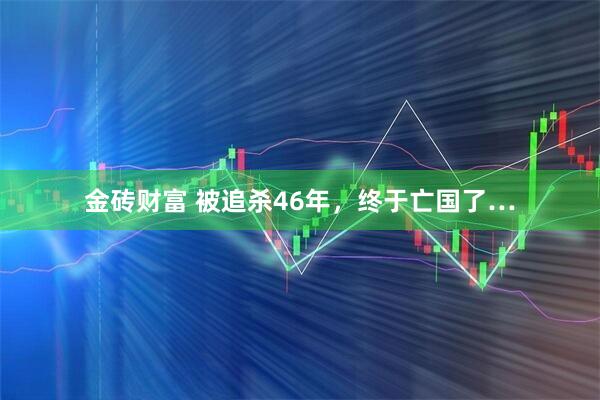

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四金砖财富,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在坚持抵抗了六年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元军。
襄阳和樊城的失守,无疑给了南宋政权一记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意味着南宋赖以起家的依靠山川地形城池防守战略的失败。
事实上,水陆交织的襄樊之地对于传统的蒙古铁骑来说的确不好攻打。然而,自大元皇帝忽必烈登台开始唱主角后,大蒙古国的治国理念、军事思想、治民方略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革新,王朝的整体发展趋势也更加符合历史潮流。反观南宋方面,依然因循守旧,不图进取,政策多变,内耗严重。虽然此时南宋的军事力量依然不可小觑,可是一个国家一旦没有了正确的思想引导,一支军队一旦没有了军魂,它离覆亡之日就不远了。
01
集中还是分散
大元打南宋的襄阳采取的是“围城打援”的战术。
六年来,南宋前前后后增援了有十几次,但几乎都被元军给一一吃掉了。
如此算来,襄阳之战中,至少有二十几万的南宋精锐或战死或被俘或投降。
纵观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的每一个王朝,即使它的常备兵力有一百万甚至二百万,但真正能拉出去上战场拼刺刀的王牌部队往往也只占它常备兵力的一半甚至四成。
蒙(元)宋开战以来,接连不断的打了不少硬仗,因此直接导致打败仗的南宋的精锐之师急剧锐减。
所以,这时候的南宋纸面上虽然还有几十万大军,但战斗力已经不可与前期相比。
为此,襄阳战败之后,南宋围绕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又开始了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南宋目前依靠的是长江防线,因此应将现有兵力集中在长江沿线的几个大城市(如鄂州、建康等)布防,依托长江天险和南宋优良水师的优势,逐城坚守把控,像襄阳之战那样,拖死元军,耗死对方。
具体的理由有二:
一是六年的襄阳之战,南宋打的苦,元军也不易(战争开销巨大,大元的国内经济也很困难);
二是长江江面辽阔,元军需要渡江而战又难以有效封锁江面,南宋依托后方基地和水师战船更容易调配兵力和输送物资。
结论——战线前移,拒敌于江,巩固后方,坚持打消耗战。
另外一种反对观点认为,不能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长江防线,一旦元军突破长江天险,江南各地没有了守备力量,南宋即刻便是灭顶之灾。
反对的理由也有二:
一是长江防线那么长,南宋兵力怎么集中?你都集中在鄂州了,元军要是不从鄂州进攻怎么办?这个风险谁来担?
二是调兵集中怎么调?都调哪些兵?由谁来任大帅统一指挥战斗?谁来担任后勤主管?
结论——各守各的领地,坚持守土有责,哪里有战火再有序支援。
在集中还是分散这个事儿上,既然问题这么多,一定要讨论。
所以,南宋朝堂里持有这两种不同观点的朝臣就开始争论不休。好像战争要等到他们讨论出结果之后才会开始一样。
而事实上,这时的忽必烈也在做抉择——是暂时罢兵还是继续推进战争。
六年围困襄阳,确实也让大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所以,忽必烈不得不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如今大元千辛万苦的拿下了襄樊之地,战争的主动权是完全在手了,暂时休兵?不甘心啊。可继续打下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呢?
公元1274年一月,指挥襄阳之战的元军统帅阿术觐见了忽必烈。
此时的阿术麾下聚集了大元四五十万最精锐部队,战线战区已经涵盖了今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
他对忽必烈说:
臣(阿术)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
——《元史》列传·卷十五
阿术的话让忽必烈想清楚了一点:当初为什么要调整战略打襄阳?不就是为了灭宋嘛!胜利的大元困难,那么失败的宋会更困难!再说了,宋的精锐部队已经基本被全歼了,仅靠一些杂牌队伍还能抵抗多久?
想到这些,忽必烈有了决定:
帝即可其奏,诏益兵十万,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
——《元史》列传·卷十五
公元1274年三月,忽必烈令宰相伯颜为主帅并增兵数十万,拟分三路灭宋:
一路以伯颜、阿术、史天泽、吕文焕等在荆湖地区集结主力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临安;一路由驻蜀元军进攻两川要地,以阻宋军东援;一路由合丹、刘整、博罗欢等分别进攻两淮,牵制宋军,配合元军主力攻宋。
三路大军各有目标,有虚有实,任务明确。
而南宋这边呢,朝堂上的诸位大人还在围着“集中还是分散”争论着…
02
想媾合成功
要看是不是符合双方的利益
公元1274年七月,南宋荒淫昏庸的皇帝宋度宗赵禥薨了。年仅四岁的小皇帝赵㬎登基(其祖母临朝摄政,贾似道依旧辅国)。
同年七月,忽必烈对誓师出兵的大元帅伯颜说:
昔曹彬(北宋名将)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元史》列传·卷十四
公元1274年九月,伯颜与驻襄元军会师后,随即对郢州(今湖北钟祥)发起攻伐。
郢州旧城位于汉水东,依山而筑,以石建城,易守难攻。同时,宋军又于汉水西筑新郢,并在两城间横铁链封锁战舰,水中密植木桩阻断舟船往来。
而且郢州的守将是被后世誉为“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另外两人是文天祥、陆秀夫)。
面对咄咄逼人的元军,张世杰没有惊慌。他令水军扼守江面,再以步军阵于江岸,并配以远程炮弩,迫使使元军难以靠近。
伯颜指挥部队佯攻了几次,都未成功。这时,他对部下说:“攻城,下策也,大军之出,岂为此一城哉!”。
然后他一边调动部队假围郢州金砖财富,一边则突然对郢州下游的黄家湾堡发动了袭击。
伯颜之所以突袭黄家湾堡,是因为这儿有道沟渠,深阔数丈,南通藤湖,大军可借此避开张世杰对汉江的封锁,拖船入湖,转而进入长江。
郢州这边的张世杰还在严阵以待,可多谋善断且狡猾的伯颜却已经绕过郢州,于十一月进逼到了鄂州(今湖北武汉)。
鄂州上一次于元军作战还要回溯到十四年前蒙哥时期的忽必烈亲征鄂州的那一仗。
那一次,在贾似道的策划下,蒙宋最后达成了和谈、休兵。如今,十几年的和平结束了,换了名称的蒙古人(元军)又打来了。
这时,南宋在鄂州的军事部署还是挺有力的:
在水路,有淮西军老将夏贵率领着几千艘战船控扼着长江要口;在陆路,汉阳、鄂州、阳逻堡都有重兵把守;而且还有一支机动的水师在长江里保持战备状态。
所以,怎么看元军短时间内也吃不下鄂州,甚至都没有多少胜算。
可是,元军的统帅是伯颜,那可是大元名将排行榜上的榜首人物啊。
伯颜不打郢州并非是惧怕张世杰,而是不想在郢州与宋军过多纠缠。
鄂州是南宋江防重地,甭管守将是谁,元军都是一定要拿下的。
于是,他令元军佯攻汉阳并营造出大军要从汉阳渡江的态势。
宋军见状,随即迅速往汉阳增兵。不想却就此中计。
原来,伯颜真正的目标是汉口和阳逻堡。
等到增援汉阳的夏贵回过神来再准备调转船头回援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元军已经很快攻克了汉口和阳逻堡,大军过江了!
夏贵一看元军已经完成了渡江,自己所率水师战船已经失去战机,则直接顺江东退了。
这一战,直接曝露出南宋在作战思路、指挥、配合以及目标、任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将领们基本上都是各成体系、各打各的,打不赢就跑,局面不利也跑。
于是乎,也就一个月左右,号称南宋最严固江防的鄂州,就兵败投降了!
元军占领鄂州之后,伯颜令吕文焕为先锋,大举沿长江东进。
这时候,忽必烈当初高规格高礼遇对待南宋降将吕文焕的作用开始凸显了。
因为南宋沿江诸将,多为吕氏旧部。
下面就是一些让人无比扼腕叹息的案例:
公元1275年正月初三,元军兵至黄州(今湖北黄冈),黄州守将降。
正月十一,元军兵至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蓟州守将降。
正月十三,元军还没有出动,江州(今江苏九江市)守将就主动联络吕文焕提前邀降了。
正月十六日,安庆(今安徽安庆市)守将也积极联络吕文焕邀约提前投降。
还有…
一个又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真格的吓坏了南宋朝堂上的孤儿寡母。
苍天啊,大地啊,如今怎么办啊,老太后像是抓住最后的一根稻草一样,哭哭啼啼的去求贾似道。

是呀,不求贾似道又能求谁呢?十几年前就是贾大人力挽狂澜的呀。
公元1275年二月一日,贾似道在王室和朝臣们的哀求下,终于答应领军出战。
这一次,贾似道不但集结了13万大军、2000多艘战船,而且还集结了由百余艘货船组成的礼品商队。
礼品商船?这是什么操作?打仗时还要谈生意?
是的,贾似道就是准备故技重施和元军谈生意。
贾似道到了芜湖(今安徽芜湖市)后,旋即派使臣先带着几船水果去“慰问”伯颜,并提出和谈的期望。
可是,这时候的大元已经不是十几年的蒙古了。
那时候,蒙哥去世,国内动荡,忽必烈还是朝臣。
现在呢,大元事业蒸蒸日上,举国上下都在为灭宋备战出力,和谈?有意思吗?
在伯颜看来,灭宋已经指日可待,与其你现在挑挑拣拣的送我钱财倒不如我大元直接取之随心所欲。
是呀,想媾合,也得具备符合媾合条件的资本啊。如今你宋国还有什么资格和条件和我大元谈呢?
于是,一边吃着贾似道送来的新鲜水果,一边伯颜果断拒绝了贾似道的请求。
求和不成,贾似道并未死心。
因为在贾似道看来,当初鄂州和谈也不是一上来就谈妥的。和谈嘛,先和再谈,一次谈不成可以多谈几次呀,反正咱礼品带的多。
就这样,贾似道在一方面主动释放一部分俘虏再次充分表明自己和谈诚意的情况下,另一方面派人继续带着礼品联络伯颜求和。
二月六日,伯颜率军到达了池州(今安徽贵池),池州守将不战而降。
这消息让贾似道很不开心。
你们这些鞑子是非要打一打才甘心吗?
劳资来时带的不只有礼品,还有刀枪!
于是,贾似道在当日令孙虎臣率7万步军列阵于丁家洲之长江两岸,又命夏贵以战舰2500艘横亘江中,自己则率后军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指挥。
可惜的是,在贾似道一心求和的误导下,这时的宋军已经丧失了拼死一战的决心和勇气。
二月十六日,在多次发动假攻击、假信息、假情报后,伯颜大军运用“回回炮”,突然对南宋丁家洲的陆军和江面的水军同时发起了攻击。
就如当初的襄阳那样,当硕大的巨石带着油火再次从天而降时,南宋军士们的心态几乎瞬时间就集体崩溃了。
于是乎,只见7万步军四散而逃,岸线阵地立马瓦解;上千艘战船你拥我挤纷纷后退,水面防御顿时消散。
丁家洲的陆军跑了,江面上的水师跑了金砖财富,贾似道也马上往扬州快速跑了。
这场被史书称之为“丁家洲之战”的战争,以南宋近乎儿戏的举动以及溃败而结束了。让贾似道飞黄腾达的“和平天使”的光环也就此沉没在滚滚长江底。
03
毁灭时刻
公元1275年,对南宋来说就是噩梦般的一年。
这一年,在川蜀地区,南宋仅有的重庆、泸州、嘉定(今四川乐山)等地,一一遭到了元军的攻击并接连战败失地。
这一年,在江东地区,南宋的鄂州、江陵(今湖北荆州)、潭州(今湖南长沙)、岳州(今湖南岳阳)等重要州府也因难以抵御元军而一一丢失。
这一年,在两淮地区,南宋的建康、镇江、泰州等江苏地域的军事力量,基本已经被元军扫平。
这一年,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已经全面暴露在元军的打击目标范围。
为此,南宋摄政太后谢道清向全国发布了“临安勤王”的诏令。
可是,此时南宋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归降大元了。所以,最后也只有在郢州的张世杰和江西的文天祥等很少的将领带兵进抵了临安。
然而,形势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张世杰和文天祥再忠君爱国又能改变什么?
公元1275年五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世杰集结了上万艘战船(估计有些夸大)在金山(今江苏镇江北)、京口(今江苏镇江丹徒镇)、瓜洲(今江苏扬州东南)三地策划了南宋最后一次军事反攻(史称“焦山之战”)。
可是,结局依然是再败。
焦山之败,让南宋最后一批能战的军队损失殆尽,临安都城亦是摇摇欲坠了。
于是,南宋朝堂诸人纷纷劝说谢太后带着皇室尽快弃都移驾海上暂避风险。
谢太后当时没有同意(因为她还幻想着能与元军求和)。
谢太后当时也没有跑(因为替她管车辇的官员小吏先跑了)。
所以,尽管在群臣的强烈弹劾下,她批准了对贾似道的清算(先是削官贬职,后来又判了流放),却一直没有明令杀之(贾似道最后是在流放途中被激愤的押解人员勒死的)。
可是,南宋在军事上已经失败到家了,还能期待得到大元的格外怜惜吗?
公元1275年七月,忽必烈向大元帅伯颜下达了夺取临安、歼灭南宋的作战指令。
公元1275年十一月,伯颜分兵三路会攻临安。
西路军以骑兵为主,向溧阳(今江苏溧阳)、独松关(今浙江安吉)进军;东路军以水师为主,沿海岸线向海盐、澉浦(今浙江海盐县南)进军;中路水路联军,向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进军。
很快,大元的西路军便攻克溧阳和独松关,一举控制了临安的北大门;东路军更是兵未血刃便完成了对临安南部的控制。
伯颜亲率的中路联军虽然在常州(常州是拱卫临安的前阵)遭到了文天祥等将领的顽强的阻击,但最后也是最悲壮的失败了(常州被元军屠城)。
公元1276年正月,伯颜的三路大军都陆续集结到了临安城下。
公元1276年二月,在内无兵源可再战,外求和称臣遭拒绝,四面围城逃跑无路径之下,六岁的南宋小皇帝赵㬎向伯颜大军献上了国玺。
在这一刻,延续了320年的赵宋,亡国了。
04
番外篇——大海啊,故乡
公元1276年五月,宋恭帝赵㬎在上都朝见忽必烈,降封瀛国公(后来出家到西藏,成为佛学大师,活到了53岁)。
同年八月,谢太后被押送到元大都,降封寿春郡夫人(在元大都活到74岁)。
在元军合围临安的前后,一些长住在或者暂住在临安的人,跑掉了。
这些人中既有皇室贵胄、朝臣将领,也有普通的军士和百姓。
往哪里跑呢?当然是向南。
时年九岁的王子赵昰和时年7岁的王子赵昺辗转温州(今浙江温州)逃到了福州(今福建福州)。
“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由于是在外领兵作战,就带着一些残兵退到了定海(今浙江舟山)。
“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作为求和使臣之一被元军扣留后,成功脱逃到了真州(今江苏仪征)。
“宋末三杰”之一陆秀夫跟随着两位小王子也辗转跑到了福州。
公元1276年六月,熟知两宋发展历史的陆秀夫效仿当年的康王赵构,决定拥立赵昰为帝,以图复国再兴。
可是,当年赵构南下时,宋还有半壁的江山国土和几十万的军队。但现在呢?南宋尚未被大元摧毁之地也就仅余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一些残兵败将。
想龙兴,想复国,难啊。
再说了,大元的忽必烈可不是当年金国的完颜晟,他哪里会给你亡国的南宋有喘息之机!
然而,张世杰、文天祥等不愿做亡国奴的将领军士闻讯后还是纷纷向福州南宋小朝廷集结。
可等到“宋末三杰”齐聚福州之后,大事还没干,矛盾遂触发了。
文天祥想北上温州建立前线督府,意在进一步收拢南宋苏浙军镇从而再返临安对敌。
张世杰认为文天祥的这想法无疑是痴人说梦,他强烈要求小朝廷立即撤往广州并做好继续退往海南的准备,过一天先讲一天。
陆秀夫呢,一直忙着替小皇帝操办登基、封官、生活起居等杂事,自己没有具体的想法和建议,任由文、张二人在争吵。
就这样子,南宋小朝廷还在争吵,大元则在此际相继平定了扬州、真州、通州、温州、广州等地(基本上都是献城投降)。
于是文天祥的北上策略也没有了,张世杰的南下广州的想法也没有了。
权衡之下,大家终于一致同意由文天祥负责把“前线督府”定在汀州(今福建长汀),并在那里拒敌。
公元1276年十一月,大元军队开始向福州“宋室余孽”进剿。
陆秀夫带着小皇帝和皇室逃往泉州,之后又逃往潮州,再逃往惠州,并开始不时的住在海上。
小皇帝赵昰很害怕。陆秀夫安慰他说,别怕,我们一起去看海。
公元1277年正月,大元进攻汀州。文天祥力战而败,被迫连续退往漳州、梅州、赣州、循州、南岭、潮阳等地。
公元1278年四月,连番的惊慌跑路和风雨颠簸,小皇帝赵昰病吓死了。
同月,陆秀夫、张世杰在冈州(今广东江门新会镇)拥立赵昺为帝,随后撤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南)。
公元1278年十一月,文天祥在潮阳五岭坡(今广东海丰县)被追击的元军汉将张弘范所部擒获。
公元1279年正月,元将张弘范押着文天祥率水陆两路元军由零丁洋(今广东珠江口外)直趋崖山(今广东江门新会区崖门镇)。
也就是在这时,身为囚徒的文天祥在敌人的战船上写下了那首名扬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而作为保卫崖山保卫皇室最后一道防线的张世杰,此刻面对蜂拥而至的元军,也再无计可施。
有部下建议说:
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之!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中,士卒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遂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馀,作一字陈,碇海中,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间为死计,人皆危之。
——《宋史》列传卷第四百五十
是呀,南宋小朝廷从成立时就连年躲在海上,躲到什么时候呢?
又退到哪里去呢?
今日倒不如与敌人决一死战痛快!
于是,宋元之间最后的一场大海战就此展开。
战斗初期,数千艘元军战船载着数十万元军向集结在一起的数千艘宋军战船数十万宋军发起攻击。
但是,由于双方兵力相等且又都是短兵相接的打法,因此谁也没有沾到多大的便宜。
于是背靠陆地的元军改变了策略——我不近攻交战了,我困住你的淡水柴薪取用之路再用回回炮远远的打你。
这一招很是奏效。
海上都是水,可是没有淡水可饮;海上都是船,可是没有柴薪可烧。
宋军坚持了十几天后,还是顶不住了。
樵汲道绝,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
——《宋史》列传卷第四百五十
与此同时,元军张弘范还使上了“瞒天过海”之计,时不时的搞歌舞奏乐晚会,装出一副暂时不准备攻击的姿态。
到了二月二十这天,当疲惫不堪的宋军又听到元军军营传来歌舞奏乐之声时,大家就都习以为常的放松了警惕。
而就在这时,早已调配好兵力做好准备的张弘范突然对宋军发动了全面袭击。
结局显而易见——已经基本丧失战斗力的宋军败了。
大军薄(逼近)中军,(张)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
——《宋史》列传卷第四百五十

公元1279年三月十九日,崖山海战结束。
是战,陆秀夫见敌人已经靠近帝船,甚至来不及说句“走吧,小赵,我们去大海”的安慰话,便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
随后,十多万南宋军民亦相继跳海而亡。
大宋王朝宣告彻底灭亡。
战后,侥幸逃脱的张世杰还谋划着想继续拥立赵氏后人为帝再图大事。可是,很快便传来杨太后(赵昰兄弟的母后)等皇室人员也已经全部投海自尽的消息。
这一日,侥幸逃脱的张世杰坐着战船漂在海上,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
是日飓风忽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柁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
不日之后,张世杰在海上风雨中溺卒于平章山下(今广东省阳江市西南的海陵岛附近)。
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张)弘范曰:“国亡,丞相(文天祥)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宋史》列传卷第四百一十八
随后,文天祥被张弘范押解到元大都囚禁。
公元1282年,多次被劝降无果的文天祥在大都英勇就义。
据说,在收拾文天祥的遗体时,发现了一封文天祥的绝笔信。信上说: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属于赵宋的王朝湮灭了,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兴起了。
说起来,好像如果没有当初南宋非常乐观的“取三京”之举,就不会又如今的下场。
可是,作为南北对立的蒙宋,又怎么能保持一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呢?
和平,从来不是拜天求神和屈膝弯腰就能够得来的。没有抑制战争的坚强国防,和平只是美妙的幻想。
汇盈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